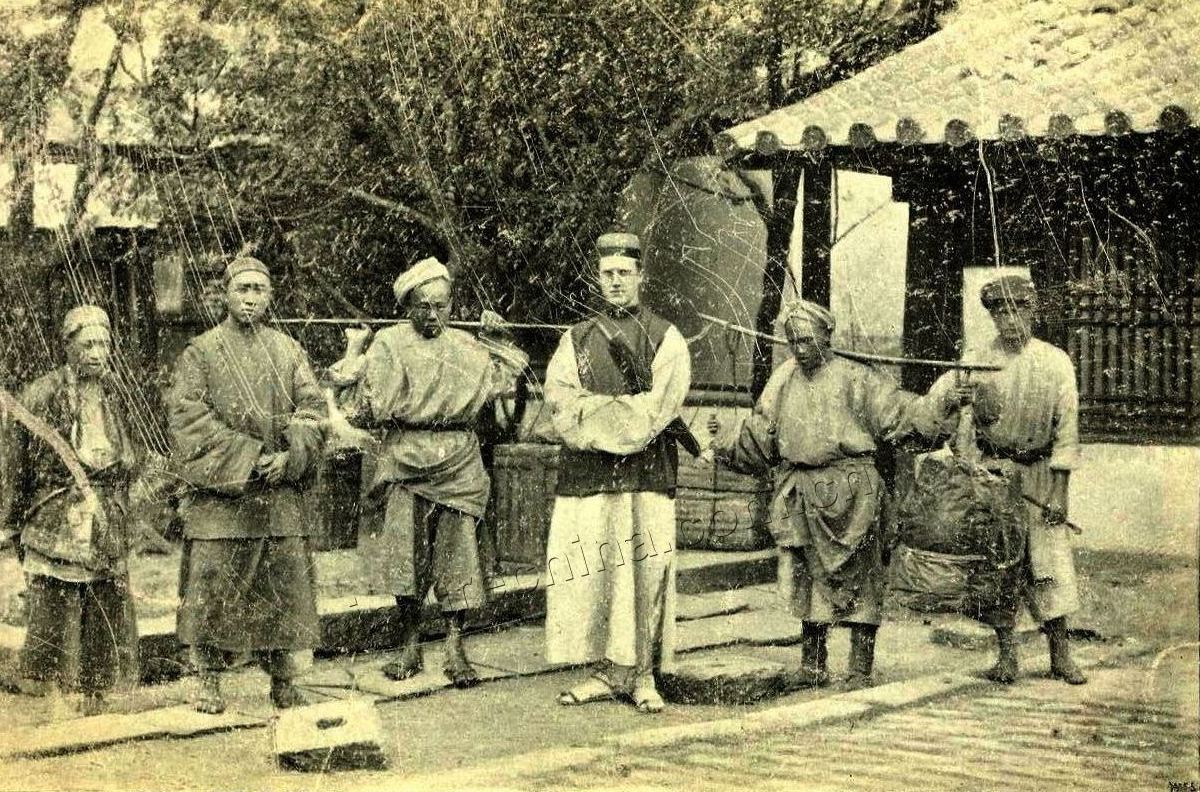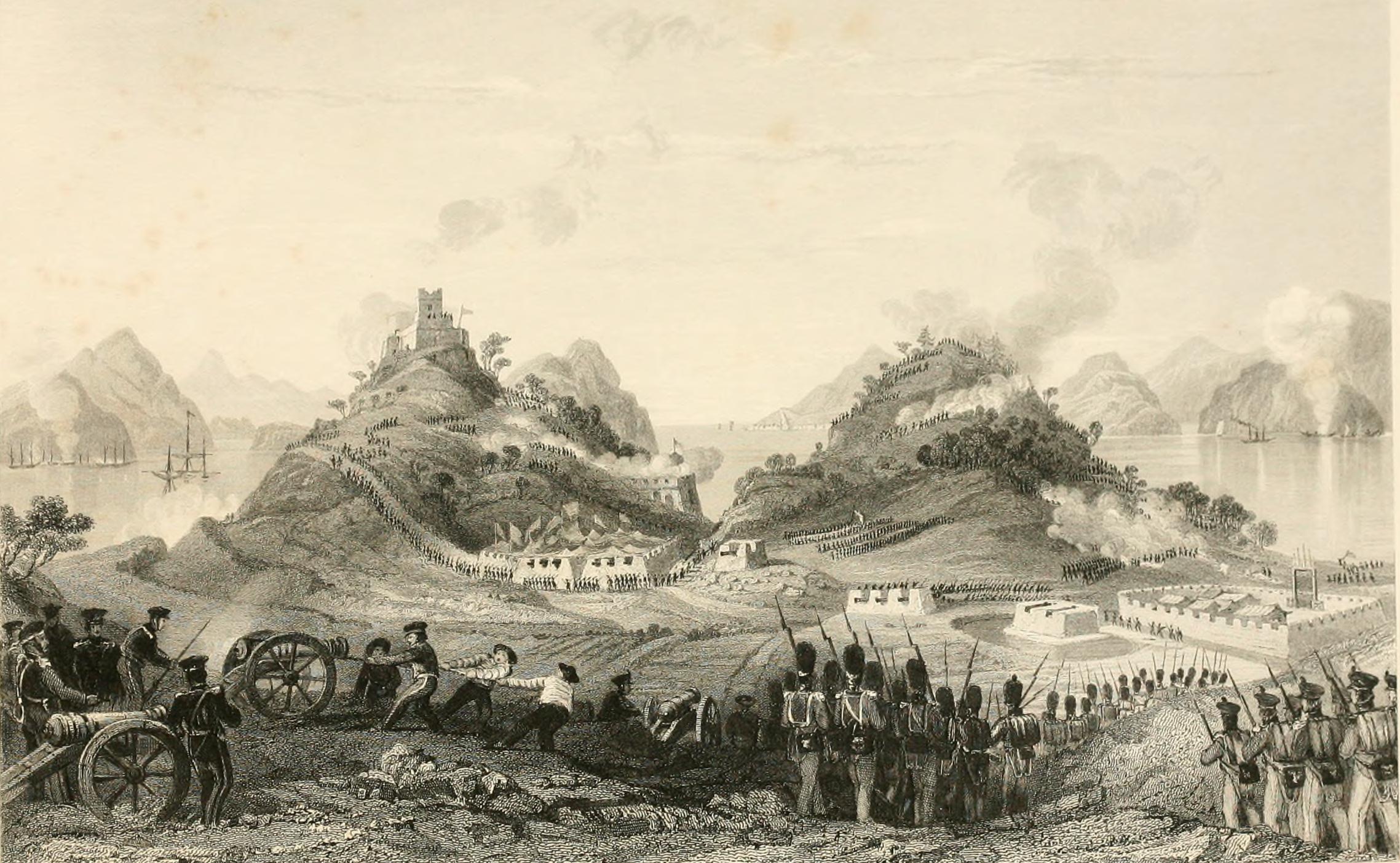駛向銅鑼灣的紅頂小巴,車頭上書「大丸」二字。熟悉本地流行樂的人們大概會想起Twins那首《下一站天后》,頭一句就是「站在大丸前,細心看看我的路」。但走遍銅鑼灣,也找不到這兩個女孩思索人生的所在,因為早在上世紀末的1998年,大丸就已經作別香港。
幾乎整個二十世紀下半葉,大丸百貨公司都是銅鑼灣的絕對地標。它位於百德新街和記利佐治街一帶,六十年代初開幕以來,風光之盛,一時無兩。雖然如今已謝幕退場多年,它的大名還是固執地留存於港人記憶裡,搭乘交通工具時也不願改口,這或多或少都與潛意識裡的大丸情結有關。
大丸情結其來有自,除了因為與這座城市相伴幾十年,更由於當年它帶來了太多「第一」和「全新」。它是香港第一家日式百貨公司,也將春風和煦的日式服務帶到香江。過去飽受商店售貨員白眼襲擊的市民,初逢大丸,自然驚豔。大丸又設有餐室和咖啡座,在先施、永安等本地傳統百貨公司,這是聞所未聞的。
大丸最大的創舉,或許就是引入了開架售貨方式。顧客不但可以隨意看、隨意觸摸,衣帽鞋褲還能任君試穿。這可真是新奇,因為其他地方的商品都和博物館文物差不多,躲在玻璃櫃中,只可遠觀決不可褻玩。戍衛一般的售貨員還會拋出一句「很貴的啊,髒了壞了都得付錢買」,惟恐顧客不被嚇跑。百貨公司竟能如此平易近人,誰也不曾想過。
開架售賣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末芝加哥的馬歇爾•菲爾德(Marshall Field)百貨。首創者塞爾福里奇(Harry Selfridge)曾是一個來自威斯康星的無名小輩,憑著過人才華一步步升為公司高層。後來他轉道英倫,創辦了以自己命名的著名百貨公司,連帶著將牛津街(Oxford Street)變成了倫敦購物天堂。而無論是在當年的芝加哥還是後來的香港,開架售賣引起的轟動並無二致。人們蜂擁而至,許多商品遭偷竊甚至哄搶。然而博弈日久,最終被改變的不是商場,而是顧客。大丸沒有從此將商品束之高閣,顧客卻逐漸習慣了開架售賣,挑選時不疾不徐,購買時理性文明。說是一家百貨改變了一座城市的消費觀,大概也不為過。
開架售賣還帶來更深遠的觀念變革。在大丸,商品觸手可及,光看不買也不是問題。過去的高檔百貨店令普通民眾望而生畏,而大丸大門常開,售貨員永遠微笑,老百姓買不起總還看得起。進來逛一逛,開開眼界、長長見識也挺好。遇上打折減價,手頭碰巧有點餘錢,買個小物什,未嘗負擔不起。窮人富人並肩選購的大丸,打破了所謂上流社會的神秘感,將奢侈品請下神壇,也令平等開放的都市文明更深入人心。
大丸的命運並非一帆風順。每當香港掀起反日浪潮,像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時,處於許多遊行隊伍必經之地的大丸,都得暫時關門歇業,以防騷擾。同是七十年代,大丸更發生過一次煤氣大爆炸,死二人,傷者多達數百人。
大丸最終退出歷史舞台,與銅鑼灣新地標的興起有關。1994年,時代廣場正式落成,令從前攤檔雲集的羅素街一帶景貌為之一新,也帶來了飛漲的地價。「時代」的時代來了,大丸的黃昏也到了。高昂租金加上激烈競爭,兼有金融風暴之下不景氣的市道,終令大丸黯然離場。《下一站天后》後半段唱:「在時代的廣場,誰都總會有獎。」而大丸的昔年榮光,只能在下小巴前喊的那句「大丸有落!」裡追思一二了。
封面圖片來源:http://www.hkitalk.net/